从家到俱乐部
From Home To Club, Vol. 1 — JAR (Xian)
12.15 2020

今年的疫情影响了所有人的原有生活。但是它让我们得以反省,自己内心最珍视的东西是什么。Shy People 推出“从家到俱乐部 | From Home To Club”新栏目,记录和尝试探讨在中国各地的小型俱乐部及以电子音乐为中心点聚集的青年文化,在遭受当前公共健康和经济危机威胁下,如何继续向前发展。第一站我们来到西安的 JAR 俱乐部。
作为历史名城,西安既拥抱过去又渴望发展新转机。在传统与当代文化冲撞如此激烈的环境下生存,JAR 放大了中国蚊型地下俱乐部普遍会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另一方面,放眼全国,JAR 又是异常的个例——它由一支本地年轻 DJ 团队创立,这帮兄弟们既是场地方同时又是演出/组织方。他们既知晓中国其他城市的现状也深知自己的能力和困境。所以,这篇采访文章算是一次具有普适性与针对性的有趣开始吧。

 在 JAR 你可以拍照,老板之一 Gunknown 也在疯狂地拍。他为此还买了相机:“我希望能记录下来这些夜晚,留下些东西,也给这些 DJ 留下些照片吧。”
在 JAR 你可以拍照,老板之一 Gunknown 也在疯狂地拍。他为此还买了相机:“我希望能记录下来这些夜晚,留下些东西,也给这些 DJ 留下些照片吧。”“主流夜店与地下场景,
可以用春暖花开和寒冬腊月来比喻。”
ASH (JAR)
可以用春暖花开和寒冬腊月来比喻。”
ASH (JAR)
“西安大多数本地的年轻人会把‘蹦迪’这两个字眼理解为去夜店这一种选项。但他们不知晓地下俱乐部的存在。提起 DJ 会联想到‘857’ ‘EDM’这类的抖音热门曲。” JAR 俱乐部的驻场 DJ 之一 ASH 如是评价西安的夜生活场地。像是荒漠中的一小片绿洲,除了 JAR,西安目前没有第二个地下电子音乐场景的发生地了。
历史悠久的“西安”即使见识再多,电子音乐依然是十分陌生的外来事物。2015年,本着在自己家乡开展可以一起玩闹的派对,活动组织方“无聊屋/ The Boring Room”(名字和著名的 Boiler Room 开了个玩笑)在创立初始的积极性和凝聚力满满,场场派对新鲜又好玩。但在收获最核心的一小戳同好和粉丝之后,市场就打不开了。在赔钱到第四个年头,哥们几个正准备放弃,突然被朋友告知有个小场地可以使用。于是大伙儿立马实地考察,晚上拉了一套设备过去试试是否扰民。无聊屋/ JAR 联合创始人 Gunknown 回忆,“我问他们怕不怕赔钱,他们说不怕,我们就开始干了。”

通常 JAR 门口会贴着当晚的时间表,这是开业那天的Line-up
JAR 开业那天,宣传只有一句“我们又回来了”的简单推送,结果来了非常多的人。“原来西安有这么多 cool kids。每个人来了都握着我的手说恭喜恭喜,弄得跟我结婚似的。” Gunknown 笑道,“一个场地对于在当地推广电子音乐这个事儿到底能起到多少作用,我想搞明白这个事情。最难的,可能还是怎么让大家来。”






JAR 的驻场 DJ 们:Darphy & ASH / RVE / Gunknown & Ziyan / 01CA & 1943 / Cash Lee & Benny
JAR 的驻场音乐担当肯定就是由无聊屋团队包揽了,因为成员个人口味有别,从80年代 House 和 Techno 到现在最新的俱乐部音乐、后俱乐部音乐都有涉猎,所以 JAR 的音乐包容性很强。基本上每个周末是一天4/4拍一天 Bass。不时也会有独立电子音乐人的 Live 演出和模块合成器的表演。

RVE:对于我是凉皮。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佐料和摆盘讲究。
1943:葫芦头!浓郁的汤汁,丰富的配料,扎实的碳水。就像 JAR 一样,有优质的音乐打底不同风格当作配料。刚开始不熟悉俱乐部文化的人可能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融入这个场景,但一旦 get 到玩法后就会一发不可收地爱上,就像葫芦头一样。
Darphy:我会把它比作卤汁凉粉。对于从来没有来过 JAR,但却蠢蠢欲动的人来说:“它看起来很屌,但是尝起来却是黑暗料理!”
Gunknown:胡辣汤。非常粘稠,不同的菜和肉丸都在里面。跟俱乐部一样,把大家揉在一起,粘在一起。
ASH:我会比喻成一罐酸梅汤。配料多种多样的同时,其口感味道带给我这个新疆人一种新奇的感觉。酸酸甜甜的味道让我会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


疫情来之前的最后一天演出,Pete (在上海工作的无聊屋成员) 和 RVE 已经带上了口罩,投影上还打着春节快乐;4月30号,疫情过后第一天正式恢复营业,JAR 请在场所有人一起喝一个 Shot,干一杯
2020年初,JAR 似乎已经走上轨道。但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关张,让每个人的干劲无处可使。“店不能开,没有任何演出。体会到父亲之前说的‘有一天你不能 DJ 了怎么办’的局面。我先是努力适应这个落差,后来好像突然觉得整个事情就那么回事儿了。我不再那么用力地强调 DJ 或者电子音乐的意义,反而是这个地方能保住了,可能才有机会让大家了解我想说的那些事情。” Gunknown 继续说道,“所以重新开门之后,这么一个小地方还显得还有点珍贵呢。能让朋友们拥抱彼此吧,我觉得特别欣慰。”
01CA 接过话题:“复工后大家更热情了,从‘开灯时间’越来越晚,刷新之前最高人数就能看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免门票的,这一举措也是在特殊时期里对热爱俱乐部的小伙伴的一种回馈,互相帮助吧。”
RVE 则强调疫情之后本地的 DJ 得到了更多的演出机会。但是问题也随之暴露——西安 DJ 非常紧缺。
面对人才不足,JAR 开始引进优质力量加入,例如武汉 GNG 团队的 Ziyan,后者既是 DJ 也是国内撰写电子音乐文章的新一代中坚。JAR 也开拓了更多的发声方式,例如进行网络直播、联合本地制作人合作项目,“这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这次疫情。” ASH 说道。


JAR 门口的乒乓球桌成了大家休息的地方,有时候早上晨练的大爷来了,他们还不走;空间非常有限,JAR 用窗帘把内外隔开,想跳舞进去,想休息的在外面;这群到大早上也没走的孩子们……
“我觉得能让大家在俱乐部里找到一种归属感
和更优质的音乐场景,JAR 是实现了。”
ASH (JAR)
和更优质的音乐场景,JAR 是实现了。”
ASH (JAR)
媒体在疫情期间开始为网络直播演出和线上派对推波助澜。虽然特殊时期有不同立场,此举可谓忽略了群体的乐趣以及对空间的想象。

在朋友家的厨房做线上直播
“音乐的细节在家里的音响是感受不到的。我可以一个人去 JAR,永远可以碰见朋友。在西安其他的空间无法满足这个条件。” RVE 补充。

无聊屋四周年那晚来了很多朋友,有人给门口这张周年海报带上了生日帽
JAR 不只是一个跳舞喝酒听音乐的地方,也成为了本土 DJ 和音乐制作人的孵化基地,Open Deck 和工作坊都会在这里不定期举办。而由 JAR 为据点引发的新一轮西安电子音乐场景,无形中化作了无聊屋团队的推动力,后者在近期增设了 The Boring Room Essential 的创意项目。我们将再作深入介绍。
当然说到最后,大家不指望 JAR 能开个十年八年,但是希望在它还没倒下前所做的每一场活动,都是高质量的。
🔗
IG@jar_xian
公众号@JAR这儿
微博@JAR这儿
📸 JAR
✒️&🎨 10000

JAR 驻场 DJ 之一/编辑 Ziyan:“如何去表现一整个俱乐部的调性?JAR 作为西安社区的中心场地,成员诸多,个性也都有所不同,因此在这个一小时的 Set 中,我以低音作为主线索,融入诸多类型的曲目来表达成员的个性。从带着浓重伦敦腔的英式说唱到声音尖锐的‘解构’,应该可以囊括 JAR 力图向这个城市推广的文化与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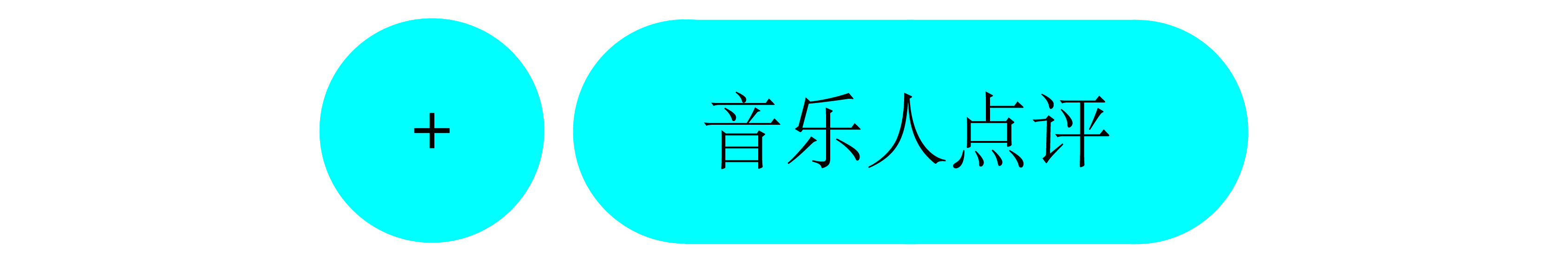
“在 DJ Booth 里演出并没有和观众产生距离的感觉,人群很 open minded。舞池的设计和室外 hang out 的设计就完全不会担心有很多人站在舞池附近的。在室内就是在舞池里,设计非常聪明。”
Yu Su (音乐人 / DJ,温哥华)
“JAR 是新俱乐部当中的榜样,精力和资源都放在了对的地方。地下俱乐部需要的东西其实就声场音响设备灯光等等这些很简单的硬件,但很多场地却没有做得很好。”
Knopha (音乐人 / DJ,上海)
“人群很 nice,奔着音乐来的,让我这种做音乐的人感觉自己有价值。”
Dirty K (音乐人 / DJ,南京)
“白酒挺凶的,爆吐一顿。”
XDD (音乐人 / DJ,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