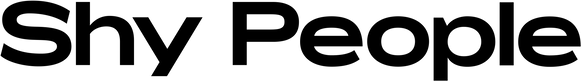《Yellow River Blue》与我们的东方
Music Review from Auntie Chen’s Column “Extraordinary Machine”
Yellow River Blue and the East on Our Own
01.22 2021
本文属于陈阿姨的音乐专栏“非凡机器”第一篇
陈阿姨是来自丽江,身在香港的音乐爱好者。
Music Review from Auntie Chen’s Column “Extraordinary Machine”
Music Review from Auntie Chen’s Column “Extraordinary Machine”

旅居加拿大的开封音乐人 Yu Su(苏玉)终于开始将发展重心投回祖国,今天在北京新厂牌 bié 发表首张专辑《Yellow River Blue》。我们趁热请来音乐爱好者陈阿姨撰写一篇乐评,解读 Yu Su 音乐中的“东方”与“乡”。
一
1997 年,就在小平去世的那晚,中央民族乐团第一次登上了美国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而在一个月后纽约时报上,全球知名的音乐评论家 Paul Griffiths 撰写了千字特稿,对这场音乐会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甚至讽刺道:“这些演奏者(虽然使用中式乐器)承袭了交响乐的每个规矩,但只有两处不同:他们穿了丝质长衫,还有他们并没有怎么给乐器调音,这因为基本上他们就没打算让乐器和谐齐奏。”同时 Griffiths 抱怨着乐团对传统民歌的演绎被前苏联艺术扭曲:“用林姆斯基高萨可夫的技法来对中国民谣旋律进行和弦写作”,摆手称最后的成品根本变成了中国人演奏他国凝视下的异国音乐。“It has about as much authenticity as the Red Army Choir.” 跟红军合唱团一样,这样的比喻包含了轻蔑与对其本质的嘲弄。
虽然这篇乐评言辞辛辣,但它在当时引起了必要的反思:“取长补短”的传统音乐革新只是为了登上金碧辉煌的西方音乐厅。但这几代艰苦卓绝的努力难道反过来抹杀了传统的本位?
二十多年过去,这种“民乐穿上燕尾服“的批判已然消散,中国传统音乐的革新早不再流连于取悦西方之庙堂。回头来看,Griffiths 这篇文章的态度反倒指涉了更深刻的问题:什么是传统?民乐是不是需要“原生态”?当他指出中国的传统音乐被俄罗斯和前苏联艺术观念“弄脏”时,那他是否听过那个真实的“传统民乐”?
保加利亚合唱团八声部的圣洁歌谣,其实根本建立在现代合唱理论和当时国家民族大统一的愿景下,原本的乡间小调最多不过两声部。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传统音乐被左派艺术和政体浸染,那也是这里生活人民的现实。如果你再追根溯源去找那个“传统中国音乐”或许将遇到巨大的困难。封建时代缺乏凝练的民乐,哪个是代表?宫廷的音乐,戏曲抑或是边疆民歌?如果说融合整理是传统民乐创新的必须手段,那对“传统”本位嫁接的执着无疑只能起到抑制创新的作用。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于一个视频:Stereotypical Music across the World。如果你跳到6:20,中国的刻板印象音乐不会是“茉莉花”或者任何一种“传统音乐”,它是 Kung Fu Fighting。1970 年代出版的 Kung Fu Fighting 根植于当时 Synth Pop 和西方舞曲中的中国元素,之后 David Bowie 的“China Girl”同样如此。这种中式 Synth Pop 的影响最后甚至反过来圈定了 1980、90 年代大中华地区的“中国风”。即使 Dick Lee 寻找了“Modern Asia”,成果也只在这种范式中踱步。
同时代 Brian Eno 和 Roxy Music 作为东方色彩嫁接西方音乐的先驱,曾谈过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当时中国出口的样板戏,同时其中明显的 Oriental Riff 来历:移民的节庆音乐、贸易往来后的变体。Kung Fu Fighting 里有种族主义?不如承认,这种异化嬗变本来就是我们东方自己发起的。自我的殖民,自发的东方主义。
这里的两个问题:“传统”的迷失和自我的殖民,是中国音乐面对东西互视时永远要面对的。
我以为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可能性就在当代的中国音乐人身上。
二


厂牌 bié 的版本,使用了艺术家苏霁的作品做封面
“The world is my home and it isn’t, but as long as there is generosity of water and mud...” (只要有丰沃的泥土和水的存在,那任何地方就像家一样)
这是中国电子音乐制作人 Yu Su 在荷兰厂牌 Music From Memory 的网站上对新唱片《Yellow River Blue》的定位。那个“the generosity of water and mud”自然和“Yellow River”是一个对象,不仅是黄河,还是故乡。一张沿着黄河而作的电子唱片。
Yu Su 之前的两张绝佳出版《Watermelon woman》和《泉出通川为谷 / Roll With The Punches》都在新专辑里找到了落脚点。“Futuro” 和 “Gleam” 里的 Dub,一面可以看作对《泉》中舞曲元素的提炼,一面可作对当下全球范围内生机勃勃 Downtempo 场景的回应。而从《Watermelon》开始的 Krautrock - House 创作,也在新专辑中开枝散叶。进一步说,轻薄的环境电子外衣,五声音阶的旋律循环、水汽氤氲的节奏和贯穿始终的“中国传统音乐”符号,如山涧组成山音一般,汇集在这部西方电子音乐的专辑中。
当然我们可以来当解剖师,研究 Yu Su 的创作灵感和音素的编织。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理解 Yu Su 说“她对 Jon Hassell ‘第四世界’概念的对抗,就藏在这张 《Yellow River Blue》 之中”。
首先来说为何批判 Jon Hassell 的“第四世界”。理解这个概念的最好方法就是想象自己走进一间唱片店,发现索韦托之声,甘美兰唱片和 Arto Lindsay 的《Mundo Civilizado》都被放在 Global 的标签下。这个 Global 指代就是“第四世界”,一个“虚构”的,从未存在的世界。之后 Jon Hassell 所做的事,即是满足他对泛世界音素的收藏癖,也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异域的/“去现代化”/神话一般的动听音乐。这种分野却离间了当地创作者的身份。“第四世界”的位置是安排好的。要是我们自己去这个位置,以为自己可以像 Jon Hassell 一样写,那只是痴梦。
Yu Su 反抗的高潮在 B 面。首先是“Melaleuca”:分段将日式 Synth Pop 和东方味 House 铺开成专辑中最流行和雀跃的曲目。City Pop 近年的挖掘,自我东方主义被西方再度挖出?那我们自己来再凝视一遍它,把它变成我们的游戏。紧接着的“Klein”则代表着创作的变形,从精致的园林景,变成泥沙,变成矿物。失真的吟唱采样和回转的声场,大量的即兴音素呼啸来去。一反其余曲目的轻盈,难以辨认的混杂。终曲“Melaleuca (at Night)”重拾东方合成器的探索,却意外地饱含深情。令人想到的唱片是 Craig Leon 为马里的 Dogon 部落做的音乐。一板一眼的键盘声和音律组成最基本的传统音乐“符号”,但是随着叠加反复,这种基础“模板”却带着专辑滑向抒情的浪潮里。
如何描述这张唱片给我的体验,我会想起 Ryuichi Sakamoto 的实验民乐唱片《Esperanto》。也是充满符号性的音素,也是错位的编织,同样为舞而作,不过《Esperanto》为现代芭蕾舞而作。借用日语世界中的常用语,这是“架空的民族乐”。“架空”并不是“虚构”,而是指在民族乐的范式上,采用非民族乐器的创作。再具体,架空是发生于民族乐上,而不是像“第四世界”的虚构总是期待召唤、模糊身份。另外“架空”导致创作者和民族乐之间的空隙,留给了音乐人空间拨弄着世界和身份的关系。让传统的东方音乐错位,一错再错,交叠后变形,接着期待着什么发生。不是描摹,而是让它出错,让它被弄脏。如同混合的黄河水不辨颜色。
三


荷兰厂牌 Music From Memory 的 LP 版本封面,使用了贵州摄影师 214 的“下河”系列的照片
“Touch-Me-Not”是专辑里第三首歌,名字来自罗马尼亚女导演阿迪娜的作品。电影探讨人对亲密关系的需求与恐惧。而 Yu Su 这首同名曲用层层叠叠的合成器组成了音幕,盘旋的音符忽远忽近,穿行环游,时而失真时而远离。那种游离感是否反应了她的体验?东方身份被西方世界的接受和拒绝,还是对故乡的爱与惧?我们离开,它是否会接受?我们回来,它仍然敞开吗?结合 Yu Su 根植于海外却又回归故土的经历不难联想这样的表达,就像是先和自己展开了战斗。而由此来看,《Yellow River Blue》则是她在战场清澈的回信。
如果说传统的“迷失”代表我们必须接受情况复杂的、混杂了东方主义和自我殖民的场景,那我们理应去勇敢接受这种庞杂,并且让我们自己成为战场。
在白人音乐的力场中,我们越来越不需要的是为那种“民族性”正名的立场。因为我们已经不想和他们平起平坐。我们要的是变成他们背后和盲区里的昆虫。我们会让他们的大语言变成小语种,在我们身上发出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