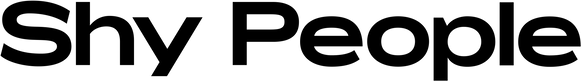酷儿夜生活作为美学解放 — 上海和北京
Queer Nightlife as Aesthetic Emancipation: Shanghai & Beijing
03.23 2021
编者按: 或许是我们孤陋寡闻,还没看到过任何关于 LGBT 群体如何融入中国跳舞俱乐部文化的文章。即使当代舞曲文化仰仗于有色人种的酷儿发展而来,LGBT 群体依然在我们这里处于被隐而不言的位置。所以……Here we are: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
—— 白先勇,《孽子》[1]
对于许多酷儿来说,我们的王国不在于一个地域,而在于夜晚的时段。夜色为我们提供了恰到好处的可⻅度,既不让我们曝露于监视之下,也不会让我们徘徊于被抹去的边缘。频闪灯映射在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在纪念和反抗中感受自由、寻找爱情、尽情做爱、并互相慰藉。



在上海,Medusa(美杜莎)便一直在重振电子音乐的酷儿根基。自2016年8月的第一场以来,Michael Cignarale 和 Sam Which(又名 Mau Mau)策划了一系列派对,意在为上海的夜生活带来魅力、幽默以及积极的性能量。Cignarale 将纽约浩室(House)音乐作为他的音乐根源,Junior Vasquez、Larry Levan 和 Armand van Helden 等艺术家都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我还没了解浩室音乐的历史之前,就已经觉得那玩意儿太他妈基了。” Mau Mau 则从2006年开始活跃于上海的地下音乐圈。 当时两人对既有的俱乐部文化有颇多不满。他们希望带来一些与规模宏大、有商业赞助的巡回活动 (circuit party)不一样的音乐体验。“我们想尝试一些更加酷儿的派对,而不仅仅是一场同性恋派对。” Mau Mau 和 Cignarale 在 Elevator(电梯)俱乐部开业的时候便一起构思了一个让酷儿回归夜生活的计划。他们受到 “A Club Called Rhonda” 等洛杉矶派对多样性的启发,同时也汲取了纽约夜生活派对女王 Susanne Barstch 般的戏剧张力,欲将这种轻浮、坎普(campy)的魅力腾挪到上海来。 Cignarale 解释道:“我们只是想看到更多的自我表达,更多的色彩与人物,让性别酷儿的幻想在俱乐 部中成为恣意的现实。带上你的 ‘真实’(realness,本意真实,其酷儿意义为某种符合特定现实⻆色的服装主题,译者注)。你的幻想是什么?我想看到这种幻想成真。”
人群的多样性是 Cignarale 和 Mau Mau 最看重的部分,而美学为其次。“在避免廉价化的前提下,我们想让自己的音乐尽量‘接地气’。酷儿舞会(ball)吸引了非常多平时在地下俱乐部⻅不到的人。” 虽然派对受到的影响是国际的,但其关注重点十分 “在地”。“很⻓一段时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通宵达旦地做 DJ,然后才慢慢开始有朋友偶尔加入我们的队伍。在派对顺利举办了近一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寻找国际艺术家,而且每年只有那么几回。” Mau Mau 指出,派对组织者往往会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去邀请国际音乐艺术家,却忽略了派对本身。Cignarale进一步解释说,关注派对本身让他们有机会分享个人的知识,探讨对派对环境的理解,并思考何为酷儿的声音:“在夜色尚早、人们开始入场之时,在半夜派对正酣时,酷儿的声音是什么?而在夜晚结束,人们或酩酊大醉、或卸下心防时,它又是什么?”
常常在 Medusa 汗涔涔的空气中舞动的是 Voguing Shanghai 的身影。这个上海舞蹈社群由舞者 Jacky Jacky 和 Shirley Milan 创立。随着电影《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以及美剧《姿态》 (Pose)等影视的普及,过去数年里 Voguing 爱好者的数量迅速倍增。Jacky 解释说,学习 Vogue 是一个成⻓和蜕变的过程,他在接触这个舞蹈之后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他从其历史渊源中获得 灵感,以抗恶劣环境的精神在舞蹈。“当人们对 Voguing 变得愈发得心应手时,你便可以感受到 ta 们破茧而出,迸发着来自内心的自信。”



而在北京,主要于招待所俱乐部举办的 “东宫⻄宫” 是另一个酷儿夜生活的焦点。它是一场俱乐部之夜,亦是一个平台,一个实验性的表演空间。“东宫⻄宫” 的创始人分别是身为俱乐部管理者的 Carmen Herold,以及北京资深的文化组织者 Geisel Cabrera。两人很早便意识到同性恋夜生活存在的问题,在2018年9月“招待所”开业时便立刻计划组织这场派对。Cabrera 介绍说:"当时很多酒吧都在尝试提供 LGBTQ 友好的夜场项目,并在其提供的服务中加入这些标签,其商业目的很明显,因为这部分人群在夜生活中的消费很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Herold 补充道:“音乐在这些派对中扮演的⻆色相当小。这些派对更多是围绕着男同志这一主要消费人群的形象。对我们而言,这些问题不容小觑。” 想要打破这种同性恋霸权(homonormative)的夜生活观念,两人不断寻找圈子中被忽视或代表性不足的人群,并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和平台来分享 ta 们的创造力。
东宫⻄宫根植于对酷儿解放现状的批判性分析,奋力追寻在政治和美学上什么才是真正酷儿的。对 ta 们来说,LGBTQ 群体日益增⻓的能⻅度是以商业化和标准化为代价的。Herold 指出:“这并不酷儿,而是 ‘范式化’ 的。我们想反对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同性恋群体观念,反对当今娱乐业中贩售的同性恋概念。总而言之,我拒绝对任何弱势群体的新自由主义化行径。” 东宫⻄宫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搜寻对酷儿性有类似理解的同道中人,尤其是女性和更具实验性的变装表演者。“很多人都知道变装文化所代表的含义和它的来源,但问题是我们总是看到千篇一律的形式。我们想要打破这样的陈规。这场派对就是要为性别操演找到新的视觉语言。” 自此,Herold 和 Cabrera 将东宫⻄宫打造成了一个实验性的空间。在这里,你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Cabrera 解释说:“它可能是怪异的,可能是异想天开的,也可能是抽象的,可能是任何东⻄。你可以看到表演性的趋向,尤其是当人们不仅因为性或性别认同,更因为其创作实践而变得酷儿时。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作为酷儿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意味着什么:打破禁忌、打破观念、打破范式、打破程序。我们想通过这场派对去探讨酷儿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DGXG edition 201910. Courtesy DGXG and Guo Yiming featuring Taipei Popcorn
除了派对本身,东宫⻄宫也是一个话语平台。ta 们组织了多场讲座和研讨会,邀请了来自芝加哥的 DJ Eris Drew 和 Octa Octa,以及来自台湾的变装皇后 Taipei Popcorn。Herold 解释说:“如果你给人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真正通过话语去认识这个群体,那你就能促成另一种层次的理解。” 对 ta 们来说,研讨和讲座能建立真实的友谊,并在个人层面提供一种与影像的联系。“互联网上有很多非常新奇和多样化的影像。但最终,要让它成为真正的体验,还是需要面对面。” 除了文化交流,主办方还希望聚焦知识生产。它不仅涉及安全空间和身份表征的问题,还旨在探究北京的本土文化场域及其独特之处。
为了让东宫⻄宫在北京举行,两位主办常常需要排除万难来构筑一个安全空间。招待所俱乐部作为活动的惯常主办方,早已被量体裁衣成一个酷儿友好的空间。Herold 解释说:“东宫⻄宫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团队中的成员都经过特殊的培训。我们开展了多次对话,谈论如何与酷儿群体正确地相处。我们总是告诉他们,要非常注意人称代词的使用,要对每个人都非常友好。我还告诉我们团队,如果看到有谁的行为存在偏差,就上前与之谈谈,但态度一定好。” 对 Herold 来说,东宫⻄宫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一个夜晚,所有的女孩们都觉得无拘无束,脱下了上衣。“这次不再是男同志们脱去了上衣,而是俱乐部里的女性们。在网上不可能有这种舒适感,因为网络并非真实的社交接触,它终究是一个不同的场域。这种真实的接触对于酷儿体验而言至关重要。” Cabreral 补充道,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种程度的自由和友善。“有很多人对我说,当 ta 们来到东宫⻄宫时感到非常放松。ta 们常常是在城市的其他空间中受到压迫的群体。”
在北京这座城市里,东宫⻄宫不断面临着不可预知的挑战。派对时常不得不进行协商和调整,但同 时也努力坚守着初心。比如与芝加哥 DJ Eris Drew 和 Octa Octa 合作的那一期,整场活动就被迫在演出前一周转移到另一家俱乐部。Cabrera 回忆说:“这提醒我们,在北京你不能把任何事情的成功当作理所当然。”东宫⻄宫团队对 Lantern(灯笼)俱乐部进行了酷儿改造,一步步落实了塑造安全空间所需的措施。“这可谓一场梦想改造计划。我们必须确保厕所是性别中立的,这也是受邀 DJ 经纪人要求我们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据此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厕所标识,将原有的厕所标识都遮盖起来。 我们在墙面上钻了孔来摆放照片,并且安装了新的照明系统。” 虽然需要管理两个空间,而且在 Lantern 俱乐部的人群混杂众多、难于控制,但最后令 Cabrera 倍感慰藉的是,俱乐部各个⻆落里酷儿们都沉醉于舞蹈中,能量也与往常的东宫⻄宫并无二致。另外,尽管审查的威胁始终笼罩着东宫⻄宫,但对于 ta 们来说正面去对抗制度从来都不是最佳选项。Cabrera 解释道,“这更像是一场博弈。有时候,在为展览选择照片时,我们必须与其他团队成员进行痛苦的讨论,决定哪张照片可能不合适展出。虽然我们总是很抗拒,但也不得不着眼于平台的⻓期目标,思考如何在这些考验中⻓久地存活下去。”

Medusa Party. Courtesy of Medusa
尽管像美杜莎和东宫⻄宫这样的俱乐部之夜并没有明确地参与政治,但它们依然是政治实践。首先,两者都探讨了酷儿的各种概念,而这恰好是中国酷儿解放问题的缩影。关于中国酷儿解放的论述,往往介于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t)和东方例外论(Oriental exceptionalism)之间,前者认为中国只是在奋力追赶世界上的自由⺠主地区,而后者则认为中国代表了⻄方可知(knowable) 与可统合(totalizable)的极限。在《两岸酷儿⻢克思主义》(Queer Marxism in the Two Chinas) 一书中,学者刘奕德指出,我们需要在不固化我们的他性(alterity)的前提下,考虑地点 (location)和语境(situatedness)的问题。他解释道,世界上 LGBTQ 群体的发展轨迹各不相同,并非在沿着全球化语境下新自由主义的唯一道路前进。事实上,把两岸酷儿身份和社区的出现完全 放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单一逻辑中去理解,简单将其解释为迟来的美国后石墙运动社会形态,是一个错误的认知。[2] 通过图像、故事以及人物的流动,中国作为普世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常常深受全球 LGBTQ 历史文化的启发和影响,但在地的土壤也让中国的社群不得不从特有的物质条件中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例如,身份政治便受到了本地酷儿派对的批判。Herold解释说:“派对并不是身份政治的演绎场,我认为身份政治是自洽的、个人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只有当非同性恋的人群中也有意支持并想要参与,这个派对才是酷儿的。” Cabrera 补充道,身份政治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是人们在所处的具体社会中为自己创造的必需品。虽然其初衷无害,但对于社会经济和历史环境不同的其他许多人来说,身份政治在全球化中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规范。“你不能只从字面上去阐述一个源自其他地方的观念,因为这样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疏远与间离。我不想疏远来自本地的表演者,或不一定认同这些想法的人。” 对他而言,我们亟需重新了解自己地区的酷儿运动起源,并尝试寻找新的语言。
中国的酷儿夜生活也充斥着复杂的能指、修辞以及各类的文化指涉,在夜色中自由碰撞着(at play)。比如东宫⻄宫的名字就来自于张元导演的同名电影,改编自王小波的短篇小说《似水柔情》。作为中国内地第一部明确讲述同性恋问题的电影,《东宫⻄宫》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在紫禁城附近公园中被捕的巡游同志男子之间发生的复杂恋爱关系的故事。俱乐部采用了这个名字,而参加夜场的人也开始玩起了文字游戏,用 “又要进宫了!” 这样的句子来暗指中国古代的奢靡王朝。类似的指涉也可以在世界各地以东亚为主题的酷儿派对中看到。很多时候,东方的形象都是女性化的,很多人便利用东方的形象来变装。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化讽刺了⻄方凝视的荒诞。但对其他人来说,这种比喻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追忆着中国被⻄方帝国主义断送的末代王朝。它触及了中国及其⻛格被赋予意义的复杂历史:这不仅包括欧洲人一开始对中国的极端幻想与迷恋,通过占有来自中国的异域商品来体现社会地位,也包括鸦片战争和其他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形象女性化和病态化的历程。对于东宫⻄宫来说,下一期的派对将重点讲述1920年代的“夜上海”故 事。Herold 解释说:“新兴的夜生活中心作为社会变革的震中,对塑造异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女性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夜生活中心是当时中国女性解放的重要场域,而她们正是第一批不用再裹小脚的中国女性。因此,我们想向爵士时代夜生活中的这类女性致敬。” 夜幕降临时是我们把内心幻想释放出来的时候,或许也是是我们最贴近潜意识中错综复杂的语义学和符号学网络之时 —— 这些语言、 图像、⻛格等塑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尤其是关于性别和性向的欲望。
通过提供一个不受监视的空间,让身体和性别在日出前获得自由,像 Medusa 和东宫⻄宫这样的俱乐部为审美抵抗(aesthetic resistance)提供了可能。Herold 解释说:"我一直主张通过审美经验完成解放。这是一种低⻔槛、间接的抵抗,但它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抵抗。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它还完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它是最关键的一种抗争。” 从历史的⻆度,许多人已经仔细讲述了酷儿的解放与夜生活的关系。从美学的⻆度来说,在一个安全空间内度过一个让人感到自由的夜晚,或许可以促成可能到来的解放——无论这种感觉是多么地稍纵即逝,这种自由是多么地遥不可及。其中,俱乐部的美学政治可以归结于电子舞曲的触感。正如学者 Luis-Manuel Garcia 所言,电子舞曲的声音绝不是无形的。恰恰相反,它通过俱乐部空间的空气震动转播抵达我们的身体,在不通过任何具体的形象或实际触摸的情况下,创造出触觉的体验。低频和高振幅的结合会冲击、穿透人体,产生共鸣。它让我们 “感受” —— 无论是在触觉感知还是情感经验层面,兼具情色与浪漫(Donna Summer 的《I Feel Love》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声波纹理作为现实世界中物体撞击、摩擦和振动的指标,也渗入了我们的听觉、视觉和触觉。触觉作为一种交互式感知模式,不仅需要身体的物理接触,也打开了一个潜在的行动场域,唤起了击打、掌掴、折断、挤压、吸吮等行为的微观叙事。[3] 这种充斥着潜在性的场域除了提供情色与浪漫的感受之外,我认为也提供了一种自由之感。人们也许并非真正自由,但如若我们置身于可以感受自由的空间,或许就可以让这种感觉引导我们的感知与行动。

DGXG 202001 edition. Courtesy of DGXG and Wenqi featuring Frozen Lolita
夜生活所带来的自由感仍与旷日持久的种族斗争史息息相关,而这段历史也不应在文化翻译中丢失。从迪斯科、浩室、电子乐到舞厅文化,从纽约、芝加哥到底特律,有色人种的酷儿,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的努力,催生了我们所熟知的夜生活文化。如果不承认种族的斗争,就不可能复原夜生活的酷儿根基。正如 Garcia 所解释的那样,作为爵士灵歌、放克和拉丁音乐的混合体,迪斯科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它通常在狭小的空间里举行,有色人种酷儿们⻬聚一堂,在城市恶劣的种族主义 和异性恋霸权的大环境下,于自己构筑的安全空间内寻觅喘息的机会。当1970年代末反迪斯科的⻛潮⻛靡美国时,对迪斯科带有性别化和种族化色彩的批判也证明了这层联系。随着迪斯科的慢慢消失,芝加哥浩室舞曲在1980年代逐渐兴盛起来。它主要流行于这座城市的酷儿和黑人俱乐部中,融合了老式迪斯科和意大利迪斯科、放克、嘻哈和欧洲电子流行乐。有人认为,迪斯科并没有死,而是以浩室音乐的形式回归了地下有色人种的舞坛。在底特律,种族对于泰科诺音乐(Techno)的发展 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这种音乐类型源自黑人中产社区,且与该市的汽⻋制造业密不可分。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任何历史文献资料都会告诉我们,尽管有少数白人、异性恋和/或顺性别者(cisgendered)的参与,舞厅文化仍一直是有色人种酷儿的领域。[4]
尽管文化总是在跨越界限的杂糅与融合中得到 “授粉”,但借用源自黑人和拉丁裔社区的音乐和舞蹈,仍然有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和文化挪用的⻛险。这些文化自身的价值与其斗争史密不可分, 当我们试图围绕它建立自己的社区时,也许要做的不仅是翻译历史,更需要审视我们与全球种族斗争的关系,并将自己置于其中。虽然在过去及当下的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压迫和抵抗频有发生,需要额外的研究与看待方式,但种族问题本身不是、也从不曾是一个纯粹的 “外国问题”。事实上,美国黑人与中国人的跨国界团结由来已久。从 W.E.B. du Bois、Paul Robeson 到 Robert F. Williams 等黑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曾支持中国的反帝运动以及中华人⺠共和国的成立。此外,中国近代史上的暴力与黑人生活中的暴力也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两者皆包含警察的暴行以及国家机器针对公⺠的军事化行为。这些也是最初激发酷儿反抗的暴力。当我们试图通过音乐和舞蹈来体会某种自由与解放的感觉时,在这样一个酷儿俱乐部的空间里或许就不难看出斗争的共同根源。听着同样的节奏舞动时,我们是否可能从感官层面到政治意识上去交叉认同不同的抗争?
夜生活带我们驶入了一个异域的时空:我们得以跳脱所生活的国家,到达一个成为松散的夜之国度。这是一个所有的社会弃儿都可以暂时躲避日间暴力的维度。夜晚里,不同的抗争融为一体,又尽欢而散。
[1] 白先勇,《孽子》(广⻄师范大学出版社), p. 7
[2] Petrus Liu, “Marxism, Queer Liberalism, and the Quandary of Two Chinas,” in 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Petrus Liu, “Marxism, Queer Liberalism, and the Quandary of Two Chinas,” in 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Luis-Manuel Garcia, “Beats, Flesh, and Grain: Sonic Tactility and Affect in Electronic Dance Music,” Sound Studies 1, no. 1 (2015): pp. 59-76.
[4] Garcia, "An alternat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club culture." Resident Advisor 28 (2014).
[4] Garcia, "An alternat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club culture." Resident Advisor 28 (2014).
☻
郗少男是居住在上海的写作者和评论人,有关艺术、媒介、和酷儿生活的写作出现在 LEAP,Untitled Folder 和 CODE 52 中。